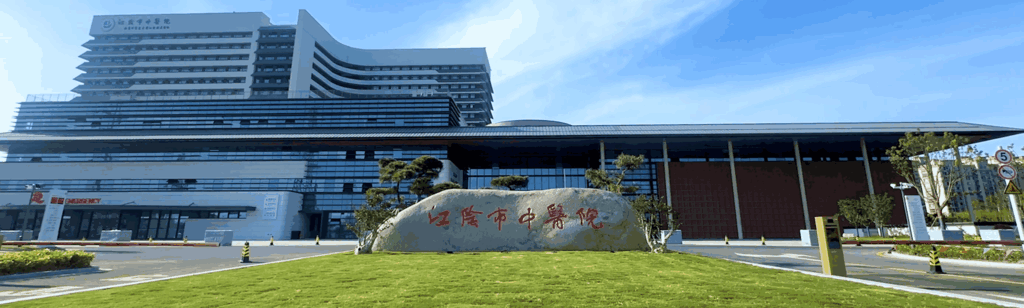“清化”法之立论依据
“清化”法之立论依据
袁师认为,根据地方区域特点和疾病谱特点,“湿、痰、气、血(瘀滞)”为临证常见病理产物,彼之不去,病焉有向愈之理?袁师常谓,“清化”之“清”,不是等同于我们认为的清热寒凉,“清”乃方法,清平、不乱之意,在临证则指轻清去实,务必和缓,力求平衡,不仅体现在临证用药的轻、清、效、廉,还要在饮食调养、养生方法中实践贯彻; “化”乃核心,是有目标和针对性的,意为性质或形态改变。
袁师以“清化”论治疾病,注重整体观,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常谓,“生病起于过用”、“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三因论”,认为在辨病求因时,三因学说可帮助我们至繁就简,易抓住疾病的本质。
“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失节、起居失常、劳倦过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强调其关键实质在于“过用”。
“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灵枢·百病始生》:“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以临床最常见的风雨寒热侵袭人体为例,说明致病因素的存在加之人体正气的虚弱,是外邪得以入侵人体形成疾患的基本原因。四时气候的正常变化及人体正气的强盛,则是保持人体健康,防止外邪为病的条件。故《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从邪气之所以能侵袭人体,产生疾患的病理角度,反证正气虚弱,抗病力下降,乃病邪得以入侵人体的前提。
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三因论”,陈氏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将复杂的疾病按病源分为外因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则包括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及虎狼毒虫、金疮折、疰忤附着、畏压溺之类有悖常理的致病因素,实际上属于致病外因的范围。三因可以单独致病,也可相兼为病,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还可产生瘀血、痰饮等新的致病因素。
《三因方》自序指出,“俗书无经,性理乖误”,“不削繁芜,罔知枢要”,因而削繁知要是其著述的目的。陈无择的三因论,是建立在“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基础上的。通过临床症状、证候类型和病理机制而探知其发病原因,并以此作为论治的依据。
陈无择临证重视胃气,辨证施治。他领悟到胃气是人身的根本,“正正气,却邪气”是医疗第一要义。他汲取前辈的临床经验,在藿香正气散、不换金正气散的基础上增添药物,创制了“温胃消痰,进食下气”的“养胃汤”, 药由厚朴(姜制炒)、藿香(去梗)、半夏(汤洗7次)、茯苓各1两,人参、炙甘草、附子(泡去皮脐)、橘皮各3分、草果(去皮)、白术各半两组成。此方一出,即广泛流传,风行一时。陈无择创制施用养胃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环境条件,温州依山傍海,冬无严寒,夏少酷暑,四季湿润,属海洋性气候,湿之为患尤多,故不畏其燥而适于应用除湿理气的平胃散、正气散和养胃汤之类。
总之,“清化”法是袁师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脾胃论》、《温热论》等历代医家经典著作,临证多法叶天士及先师柳宝诒等温病大家之法,结合江阴地域地理、文化、饮食等特点,认为江阴地域患者多痰湿体质,或气血瘀滞,诸多疾病可辨证为痰湿证,或兼夹痰湿证,或兼夹气滞血瘀证。临床用药多护及脾胃,脾清则痰湿无居所;常以清化痰湿气血为主或辅佐以清化,使得痰湿去、气血和;用药轻灵醇和,不伤本虚之正气。“清化”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