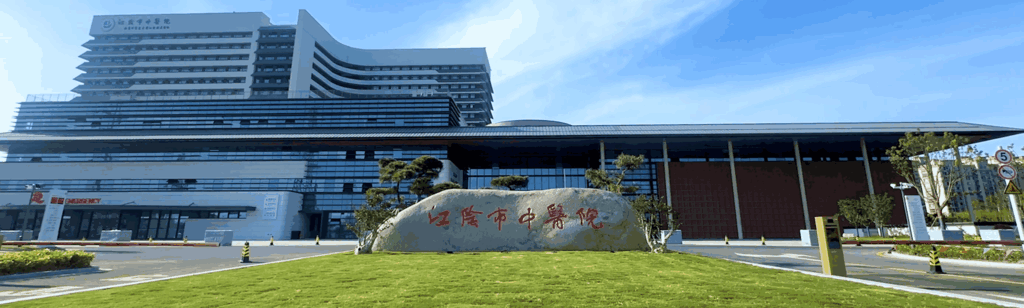袁士良教授从“清化”论治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经验总结
袁士良教授从“清化”论治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经验总结
袁保,杨静,翟金海,龚伟,花海兵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阴附属医院 江苏江阴 214400)
摘要:袁士良教授行医40余载,在辨治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方面经验丰富,见解独到,常以整体辨证结合“清化”论治,袁师总结关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中医证型有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弱证、胃阴不足证,其中以脾胃湿热证最多见,脾胃虚弱证次之,二者相兼者亦多见,肝胃不和及胃阴不足少见,其中各个证型均可兼夹胃络瘀血证。治疗以清化论治,常用香砂六君子汤或黄连温胆汤为主加减治疗该病的脾胃虚弱证及脾胃湿热证,或二者合方加减治疗相兼病证。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清化论;临床经验;袁士良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是慢性胃炎的主要致病因素,长期感染后,部分患者可发生胃黏膜萎缩和肠化,根除Hp可使胃黏膜炎症消退,慢性炎症程度减轻,成为治疗慢性胃炎的关键环节之一。随着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中医药有望为Hp感染治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江苏省名中医袁士良教授数十年来潜心研究,开创“清化论”学术思想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对本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临床疗效肯定。袁师认为“脾胃湿热”导致“湿热生虫”,“脾胃湿热”是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发病的基本因素,治疗以“清化论”学术思想为主,兼以养胃调治。笔者跟随袁师侍诊学习,聆听袁师对该病的基本病机和治法的认识,总结出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方法,现总结如下。
1.病因病机
本病多无典型及特异的临床症状,表现为上腹部饱胀或疼痛,嗳气等,根据其表现,将其归属中医“痞满”、“胃脘痛”“嘈杂”等范畴。袁师结合40年行医经验,认为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应以治本为主,抗幽门螺杆菌为辅,临床注重辨证论治。袁师认为该病病因主要涉及外邪侵袭、脾胃虚弱、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痰湿内蕴、瘀血阻滞等,病位在胃,涉及脾、肝。病机是脾胃受损,或肝失疏泄,或外邪(HP)侵袭,导致纳运失常,湿热内生致HP感染,或HP感染后内生湿热,病久郁热则伤及胃阴,或伴胃络瘀血。袁师总结关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中医证型有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弱证、胃阴不足证,其中以脾胃湿热证最多见,脾胃虚弱证次之,二者相兼者亦多见,肝胃不和及胃阴不足少见,其中各个证型均可兼夹胃络瘀血证。
2.辨证论治
2.1健脾益气清化
脾胃为仓廪之官,主受纳和运化水谷,若饥饱失常、饮食不节、劳逸适度或久病脾胃损伤等,均可引起脾阳不足,脾阳虚则胃腑亦不能受纳腐熟水谷,胃失和降,气机运行失常,故可见胃脘胀满或隐痛,胃部喜暖喜按,大便稀塘,乏力,舌质淡,边有齿痕。食少,气短,懒言,呕吐清水,口淡,脉细弱。袁师认为脾胃虚弱,或脾胃虚寒,或寒热错杂,施以健脾益气清化,和胃止痛。方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太子参15g、炒白术15g、茯苓10g、陈皮6g、法半夏10g、炙甘草10g、木香10g、砂仁6g、煅瓦楞子15g、牡丹皮6g、炒枳壳10g、姜竹茹6g、炒谷麦芽各15g。全方以健脾益气为主,和胃止痛,清化为辅除以寒热错杂之症。袁师以此为主方治疗脾胃虚弱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取得满意临床疗效,现代研究已证实其中的香砂六君子汤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可增强胃黏膜的屏障保护功能[1]。袁师认为脾贵在运,益气要先健脾,脾胃运化正常,气血才能生化无穷,脾胃健则气血旺。故袁师常以香砂六君汤健脾益气,其中白术味甘而温,健脾运脾,以促生化之源,古有“脾旺而不受邪”之论,气血充盛则诸痰难生。袁师认为久病胃阴必虚、或饮食不节耗损为阴,太子参较党参更能护养胃阴,因此也常用太子参益气养胃。此型患者若HP感染较重,超过+++,则可以加用黄连3g、蒲公英15g具有杀虫健胃之功效[2]。袁师认为少剂量黄连不仅不会伤胃,既能杀虫,还具有养胃的作用。
2.2清化理气和中
脾胃运化失司,水湿内蕴,酿生痰浊,困阻中焦,使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为痞满,气机阻滞,不通则痛,发为胃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浊气在上则腹胀。”故可见胃脘痞闷(堵闷)或胀痛,胃底灼热,口苦,口臭,恶心或呕吐,尿黄,胸闷。袁师认为Hp感染当属“邪气”,脾胃湿热证的Hp感染率高,与脾胃生理特性有关。胃喜湿恶燥,主受纳、腐熟,以通降为顺;脾主运化、转输,以升为健。脾胃升降相因,燥湿相济,才能维持水谷的消化吸收。若这种关系失调,就会出现病变上的相互影响,造成湿热之邪Hp的生长、繁殖,Hp感染可导致脾胃湿热,而脾胃湿热又为Hp感染提供了有利生长繁殖环境。正如薛生白《湿热病篇》所云:“太阳内伤,湿邪停聚,客邪再致,内外相引,故病湿热”。 《兰室秘藏·中满腹胀论》提出:“脾湿有余,腹满食不化”,治以清化理气和中。方用黄连温胆汤加减。黄连3g、法半夏10g、陈皮6g、茯苓10g、枳壳10g、姜竹茹10g、生甘草6g、木香10g、太子参10g、炒白术10g、煅瓦楞子10g、牡丹皮6g、炒谷麦芽各15g。研究证明,黄连温胆汤可显著降低炎症细胞因子IL-8的水平,改善胃粘膜病理状态。说明黄连温胆汤可能通过根除HP,影响细胞因子IL-8,改善胃粘膜的病理变化,从而改善慢性胃炎症状[3]。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黄连对HP具有显著抑杀作用,具有抗炎、保护消化道黏膜、促进损伤组织的再生与修复的功能[4]。甘草具有和中缓急止痛、解毒、调和药性的作用,甘草浸膏对大鼠实验性胃溃疡具有保护作用,甘草次酸同时也具有抗炎的作用[5]。枳实能够兴奋胃肠道平滑肌,促进胃肠蠕动增加胃肠道排空速度及推进小肠规律运动[6]。黄连温胆汤治疗 HP相关性胃炎,既遵循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法则,又与现代医学 HP 相关性胃炎的基本治疗原则相符合,且疗效确切,不仅可以改善临床症状,还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如患者湿热或痰湿较重,HP感染较重,超过+++,则可以加用黄芩10g、浙贝母15g以增强治疗效果。
2.3疏肝和胃理气
肝与胃是木土乘克关系。情志不遂,抑郁恼怒,肝失疏泄,肝气郁滞,横犯脾胃,脾胃升降失常,可发为痞满或胃痛;忧思伤脾,脾气受损,脾失健运,胃腑失和,亦可发为痞满与胃痛之症。此型可见胃脘胀满或胀痛,情绪因素可诱发或加重,可伴胁助胀痛,嗳气,嘈杂,反酸,胸闷,食少,大便不调,心烦易怒,睡眠差。袁师认为此肝郁气滞,肝胃不和证,治以疏肝和胃理气,兼以清化。方用柴胡疏肝散合百合汤加减。柴胡10g、香附10g、枳壳10g、炒白芍10g、炒白术10g、生甘草6g、苏梗10g、陈皮6g、佛手10g、百合20g、乌药10g。全方疏肝和胃理气清化。百合用量较大,主要用于治疗气郁化热导致的胃痛。袁师认为方中百合味甘性微寒,养阴益肺,清化之效佳,《神农本草经》谓:“百合,味甘平,主邪气腹胀心痛”,乌药味辛性温燥,行气止痛,温散之力强,袁师认为二药相伍,一凉一温,一走一守,润而不滞,燥而不过,利于脾胃功能的恢复;并强调可根据病证寒热多少不同灵活调整用量,可不局限于气郁化热之胃痛,对胃气不和之胃痛等均有较好疗效。合柴胡疏肝散共可疏肝和胃理气,兼以清化养阴。清代名医叶天士强调“凡醒胃必先治肝”。肝气疏泄条达,则胃不受侮而胃气通降,胃疾乃愈。如兼以肝胃郁热,加之HP感染较重,可加黄芩10g、郁金10g,黄芩苦寒,清胃泄热,柴胡、黄芩相配,行肝气,清胃热,郁金辛苦微凉,为血中之气药,一则能降胃气,行肝郁,二则气为血之帅,久病必瘀,故祛瘀必佐理气之品。
2.4养阴益胃清化
胃为六腑之首,嗜食辛辣肥甘厚腻,饮酒过度,脾胃乃伤,最易耗伤脾气与胃阴;或肝郁化火,火郁日久,化火伤阴;或脾胃内生湿热,湿热暗劫胃阴;或过用温燥化湿之品耗伤胃阴所致。此型可见胃脘灼痛或隐痛,嘈杂,伴大便干燥,饥不欲食,口干,消瘦。或在肝郁气滞化火证之后期及脾胃湿热证之后期各个证型相兼为病。袁师谓此胃阴不足证,治以养阴益胃清化。方用沙参麦冬汤合百合汤加减。北沙参10g、麦冬10g、生地15g、玉竹10g、百合20g、乌药10g、佛手10g、炒白芍15g、生甘草6g。“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强调温燥治脾,柔润治胃。叶天士曾说:“胃为阳土,宜凉宜润。”在临床中,治疗胃阴不足者,宜用“甘凉”,以增其液而善其阴。此吴鞠通借鉴叶天士之法变化出了沙参麦冬汤,具有养阴益胃清化之功。百合、乌药即百合汤,袁师认为方中百合味甘性微寒,养阴益肺,清润之效佳,合乌药行气止痛,诸药合用养阴益胃清化,促使胃津充沛,既可用治胃阴不足,且可用治脾阴不足。现代研究证实沙参麦冬汤对胃粘膜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且具有显著增加胃粘膜分泌的作用[7]。如感染较重,可加用黄连3g乌梅10g,即可以益胃养阴,待津液来复胃气和降,不攻而宿满自除,乌梅、黄连又可以杀虫灭菌。
2.5胃络瘀血证
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日久,必致血瘀。瘀血内停,阻滞气机,脾胃升降失调而致痞满、胃痛。《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谓:“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聚瘀''。此型可见胃脘胀满,刺痛,痛处拒按,痛有定处,舌质暗红或有瘀点、瘀斑,或伴黑便,面色暗滞,脉弦涩。袁师认为单独的胃络瘀阻证相对少见,可作为各证型兼夹证,通过方刻或药物的加减进行治疗,本病易反复发作,病程较长,而“久痛入络”,必致血瘀,如兼夹胃络瘀阻,在主方基础上配合丹参饮和/或失笑散化裁,选用丹参15g、檀香10g、生蒲黄(包煎)10g、五灵脂10g、三七粉3g等药物,行气活血,气畅血行,诸疾自愈。《丹溪手镜》论述痞满“治宜升胃气,以血药治之。”丹参、檀香二味取丹参饮之意,气血双调,活血行气,通络止痛,以达活血消痞之效,预防胃粘膜萎缩癌变。胃痛较重可加用蒲黄、五灵脂。蒲黄、五灵脂合用则成失笑散,气血兼调,活血祛瘀、散结止痛。其中蒲黄、五灵脂还有止血功效,能保护胃黏膜,防止出血。三七粉冲服,化瘀止血、活血定痛,亦可补虚强壮。袁师认为活血化瘀药物对增生性病变有不同程度的软化和促进作用,活血化瘀药常常在调节机体反应性的基础上又直接或间接地达到抗菌目的。现代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药可改善血液流变学、调节免疫保护胃黏膜屏障、调控基因、诱导细胞凋亡防止癌变等[8]。
3.总结
祖国医学并无Hp相关性慢性胃炎的名称,现代诸多中医学者认为可将Hp归属于“邪气”范畴,或称“毒”,且多“湿热”的性质。袁士良教授对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主张“清化”立论治疗此病。“清化”法是袁师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脾胃论》、《温热论》等历代医家经典著作,临证多法叶天士及先师柳宝诒等温病大家之法,结合江阴地域地理、文化、饮食等特点,认为江阴地域患者多痰湿体质,诸多疾病可辨证为痰湿证,或兼夹痰湿证。临床用药多护及脾胃,脾清则痰湿无居所;常以清化痰湿气血为主或辅佐以清化,使得痰湿去、气血和;用药轻灵醇和,不伤本虚之正气[9]。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虚无以抗邪,或邪气过盛,则人易感邪而发病。袁师论治疾病,注重整体观,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常谓“生病起于过用”、“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三因论”,认为在辨病求因时,三因学说可帮助我们至繁就简,易抓住疾病的本质。袁师常谓“生病起于过用”,饮食不节,过量饮食、过量饮酒、嗜食辛辣刺激之物、频繁的饮食自倍,导致脾胃运化失常,是发病的外因,“两虚想得,乃客其形”,外因伤及脾胃,脾胃运化功能不能自复,长期恶性循环导致脾胃虚弱,脾虚生痰,痰湿郁久化热,故可致脾胃湿热,“脾胃湿热”又导致“湿热生虫”,乃发幽门螺杆菌感染,故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临床以脾胃湿热证、脾胃虚弱证最多见。组方方面袁师常以香砂六君子汤或黄连温胆汤为主加减治疗该病的脾胃虚弱证及脾胃湿热证,或二者合方加减治疗相兼病证。祛除病因是预防调护、疾病趋于愈合的基础,袁师认为“湿、痰、气、血(瘀滞)”既为发病原因,又为发病机制,是临床辨证施治的靶点,结合体质特点,审症求因、圆机活法,施以“清化”,祛除病因,以达标本兼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傅智敏,朱曙东.香砂六君子汤对大鼠急性胃黏膜损伤的保护作用[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4(4):52.
[2]陈正,王庆其.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性胃部疾病概况[J].中医杂志,2008,49(12):1129.
[3] 杨国红,胡研萍.黄连温胆汤治疗HP阳性浅表性胃炎(脾胃湿热证)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04,13 (12)804-805.
[4] 张存钧,蒋振明,张镜人.中药对幽门螺杆菌抑菌作用的体外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2,5(3):168 -169.
[5]周秀彦,郭文栋,王琦,等.胃幽净胶囊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疗效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20(12):934-935.
[6]黄武,陈茜.黄连温胆汤治疗消化性溃疡45例[J].河南中医,2014,34(9):1777-1778.
[7]曹西华,候家玉.沙参麦冬汤对大鼠胃粘膜保护作用的机理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5,11(5):1-3.
[8]刘远林.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疗效及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05,13(2):127-128.
[9] 花海兵,向培,夏秋钰等. 袁士良清化立论诊疗经验述要[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6):122-124.